为什么日本选择了战争 作者/季卫东
发表于 ・ 资讯中心

— 揭开日本历史演进的深层密码
1984年10月初我到日本京都大学留学,不久就在校园附近百万遍知恩寺举行的秋季旧书大集市上以非常便宜的价格购得一套小学馆在1970年代前期出版的《日本的历史》(计32卷)。虽然其中有些内容略显过时,但对一个并不专治史学的外国人而言还是够用的。
二十四年后回国之际,因为需要托运的专业书籍太多,就把那套通史全部扔掉了。现在,讲谈社在二十一世纪初出版的《日本的历史》(计26卷)中文版萃取10卷翻译印行,或多或少弥补了我手边缺乏日本史书的遗憾。
透过表面的现象观察潜在的动机和逻辑关系,把时间序列与空间结构结合起来进行社会的立体化分析,我以为是“讲谈社•日本的历史”系列的显著特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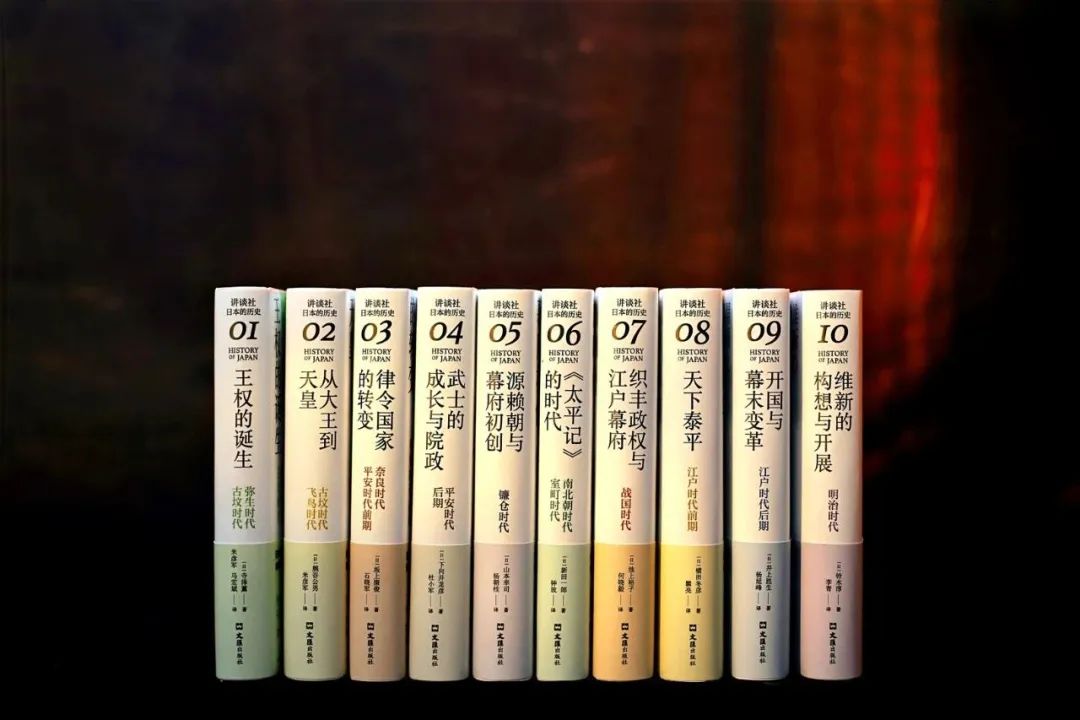
这套书各卷均为相关断代史领域一流专家的个人专著,对史实的描述更具有连贯性、整合性,并且时有史论的阐发以及贯穿其中的批判理性显得灵光乍现。
出于个人的兴趣,在阅读这套书时我特别关注三个问题:
1. 在中华帝国主导的东亚册封外交和华夷秩序之外,日本为什么能形成一个独立的小型朝贡体制?
2. 通过“大化改新”曾经建立起来的律令制官僚国家,究竟怎样才蜕变为封建制领主社会,以致“明治维新”又把版籍奉还、废藩置县作为现代化的首要目标?
3. 日本固有的法律和审判有哪些特征决定了制度变迁的路径?
在这里结合上述问题意识简单谈一点感想。
《汉书》等史料以及1784年在日本出土的“汉委奴国王”金印都证明,倭王权与中原王朝之间的交往源远流长,至少邪马台国的女王卑弥呼和倭五王是正式接受了中国皇帝册封的。

本来东瀛列岛四周环海,存在天然的安全屏障,让大陆帝国产生鞭长莫及之感,那为什么倭王权还要主动拜结藩属关系呢?
曾经任职宫内厅的熊谷公男教授在记述古坟时代和飞鸟时代的第2卷《从大王到天皇》中给出的理由是:
1. 借助中华帝国的权威来加强倭王权的地位,维系内部的君臣关系;
2. 吸纳大陆的先进文化、技术、制度以及物质,尤其是通过垄断这类资源的分配来掌控列岛各地的首领。
然而当倭王权已经巩固时,第一种理由就无足轻重了。当倭国可以通过与朝鲜半岛之间的交通线获得必要的资源时,第二种理由也会大幅度减弱。于是乎,倭王权渐次产生了脱离对华朝贡体制的意志,而使意志转化为行动的关键在朝鲜半岛的局势。
古代朝鲜的各国面对中华帝国极其强大的压力,始终处于战战兢兢的状态,也很容易出现合纵连横的战乱,并且一旦有事就不得不向倭国求援。因为自然形成的“海上万里长城”,只要朝鲜半岛具有对华的某种独立自主性,大和民族就可以高枕无忧,所以倭国势必介入半岛事务,抓住朝鲜各小国的软肋逼迫其从属、朝贡于自己,并用武力支援来交换产自大陆的文化、技术以及物质资源。
本来朝鲜各国大多已经是中国的藩属国,为了敷衍倭国不得不展开“二元外交”——同时承认对中国皇帝和倭王权的朝贡。在条件不成熟时,倭国自身也要推行复杂的二元外交,玩弄规范的语言游戏——表面承认中国为宗主,但背地里却自称宗主。用坂上康俊教授的表述,“在面对大唐和在面对国内、新罗、渤海时使用两副不同的面孔”。
但是,一旦条件成熟,倭国就会拉起自我中心的“小中华圈”,力争独立于中国在东亚建立的华夷秩序之外。
为了形成和维持上述机制,倭王权的首要任务当然是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以便对内统一东瀛列岛,对外挺进朝鲜半岛。

正像下向井龙彦教授所分析的那样,到公元8世纪,律令制下的日本按照“一户一兵”的方式进行征兵,已经可结集起20余万人的军队。考虑到当时总人口只有600-700万,这的确是令人震惊的武装规模。
实际上,日本建立编户制、班田制的目的就是要维护一个庞大的军团,奉天皇为最高军事指挥。由于本国防卫几乎不太需要用力,如此畸形发展的士兵队伍必然带有侵略性,始终以新罗和中国为假想敌。
当然,强大的武装力量也使日本进一步加强了独自建构朝贡-册封体制的底气。虽然后来律令国家为了减轻财政负担而有裁军之举,但旋即武士阶层登上历史舞台,进而走向武家政权。可以说,日本军国主义的历史根源就在这里。
史料证明,倭本位的“小中华圈”从公元405年倭王支持百济的人质腆支继承王位起开始形成。起先的意图仅仅是为了与半岛北部比较强盛的高句丽对抗,并且希望从中国皇帝的册封中取得与高句丽同等的地位。
倭王为了促使中国统治者赐予“都督诸军事”称号,举出包括金官国、加罗的北大加耶地区、秦韩、慕韩等在内的任那以及百济、新罗为倭国藩属作为依据,实际上是想让中国承认他拥有对高句丽领域之外的朝鲜半岛的军政统辖权。
由于百济、新罗均为独立国家,百济还得到中国册封,所以当时的中国王朝统治者拒绝了倭王的诉求。为此,倭王决定脱离中国的册封体制并开始使用“治天下大王”称号和“日本”国名,到7世纪更采用“天皇”称号,旨在树立万世一系统治天下的具象化终极权威,并且全然不受中国式天命论和德治思想的约束。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日本建立的“小中华圈”里,任那这个朝鲜半岛上的伽耶诸国作为藩属的典型或者象征性符号始终具有的重要的意义。即便在任那被其他国家消灭之后,日本也长期打着“复兴任那“的旗帜不断向周边小国施加影响并牟利,甚至迫使已经成为藩属的新罗派遣官吏充当任那使臣、另外再以任那的名义追加一份贡品(任那之调)。
后来,又以列岛内部的异族虾夷、隼人等来代替外部的任那作为朝贡国,反复上演册封与藩属关系的活剧,以向本国臣民作君临天下之秀。在这层意义上可以说,古代日本也属于一种以武力进攻和武力支援为手段来推行朝贡贸易的“剧场国家”,任那则或明或暗在其中扮演作为一个”托儿“的角色。时至今天,东亚又开始风云变幻了,那个任那还会在什么地方借尸还魂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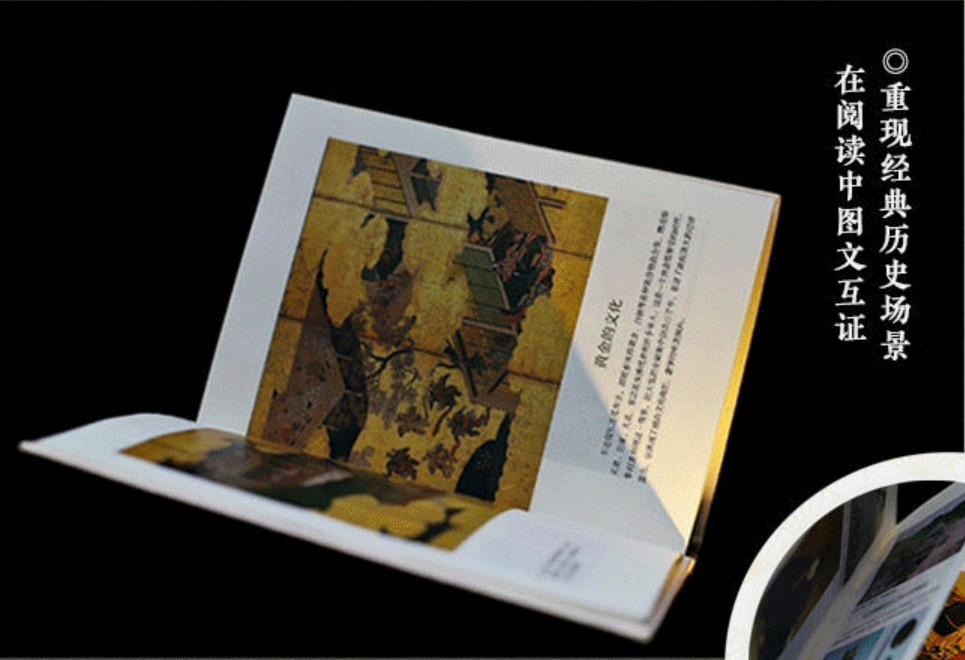
从“讲谈社•日本的历史”丛书可以看到,公元5世纪的倭王权具有联合政权的性质。以倭王室为中心,与葛城、和珥等大和豪族以及筑紫、吉备、出云、纪、上毛野等实力派地方豪族结成联盟进行统治。
地方豪族为倭王室效力,作为回报可以获得经由朝鲜半岛引进的大陆先进文化、技术以及产物,特别是当时极为重要的铁资源。在这里,互惠构成秩序的黄金律,礼尚往来的酬报关系维系着政权的稳定。
与这种联合政权的属性相关,倭王的即位仪式与后来的天皇即位仪式不同,需要经过群臣推举新王的程序。这意味着大王不能仅凭自己的个人意志决定继任者;这也意味着如果倭王没有获得群臣的推戴,其正统性就会受到质疑;这还意味着在即位仪式上大王与群臣必须互相承认,宛如重新缔结联盟的契约。
到了公元6世纪上半叶,倭王权以镇压地方豪族的叛乱为契机开始推行集权化,借助氏姓制、国造制、部民制加强对社会的控制。当然,对朝鲜半岛用兵也成为加强倭王权力的一种重要的驱动装置。
在7世纪上半叶,围绕推古天皇的王位继承爆发激烈的持续争论,群臣不得不从先王遗诏中寻找解决问题的线索和根据,这意味着前任大王的意志开始变得更加重要。就在这样的背景下,统治者逐渐倾向于采取禅让的方式转交王位,在事实上绕开了群臣推戴环节。
于是,前任大王对王位继承终于获得决定性影响力,并且确立起倭王的主体精神。正如坂上康俊教授所说,“太上天皇是为了让皇位继承更加顺利才存在的,……这是日本独自设计出来的制度。然而,倘若皇太子制度本身很稳定,那么太上天皇制度也就画蛇添足了”。以前任的大王或天皇让位来决定继任者的方式,实际上也为后来的“院政”以及权力二重结构留下了一道意味深长的伏笔。
随着倭王主体性的增强,在天皇与群臣之间毫不避讳的互惠性关系的基础上,开始建构一种等级化组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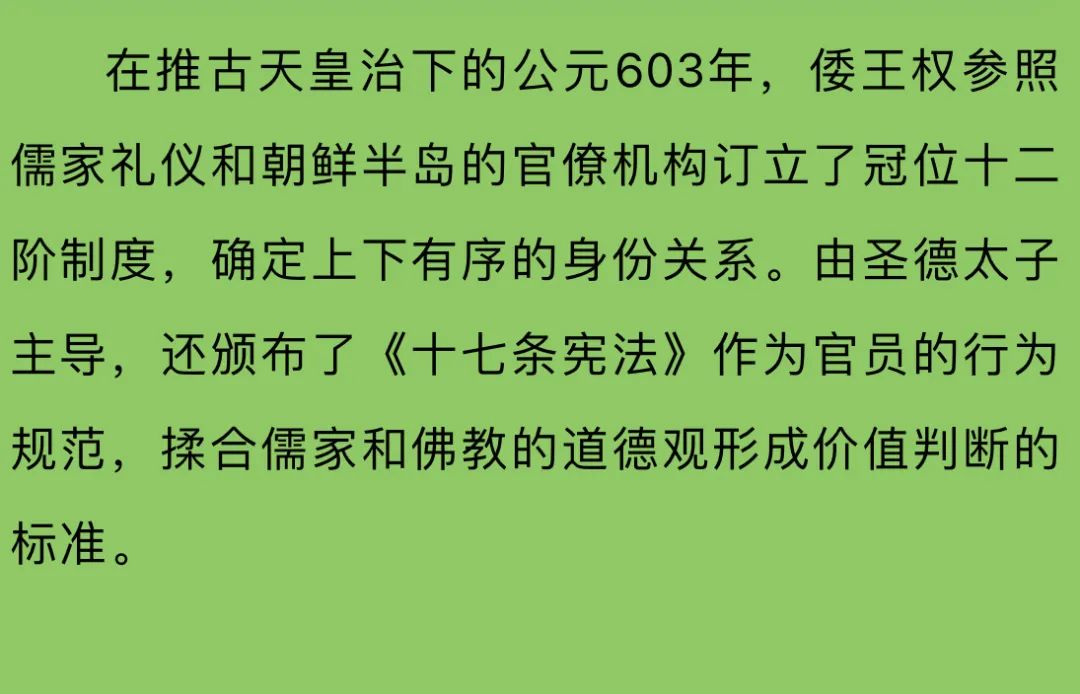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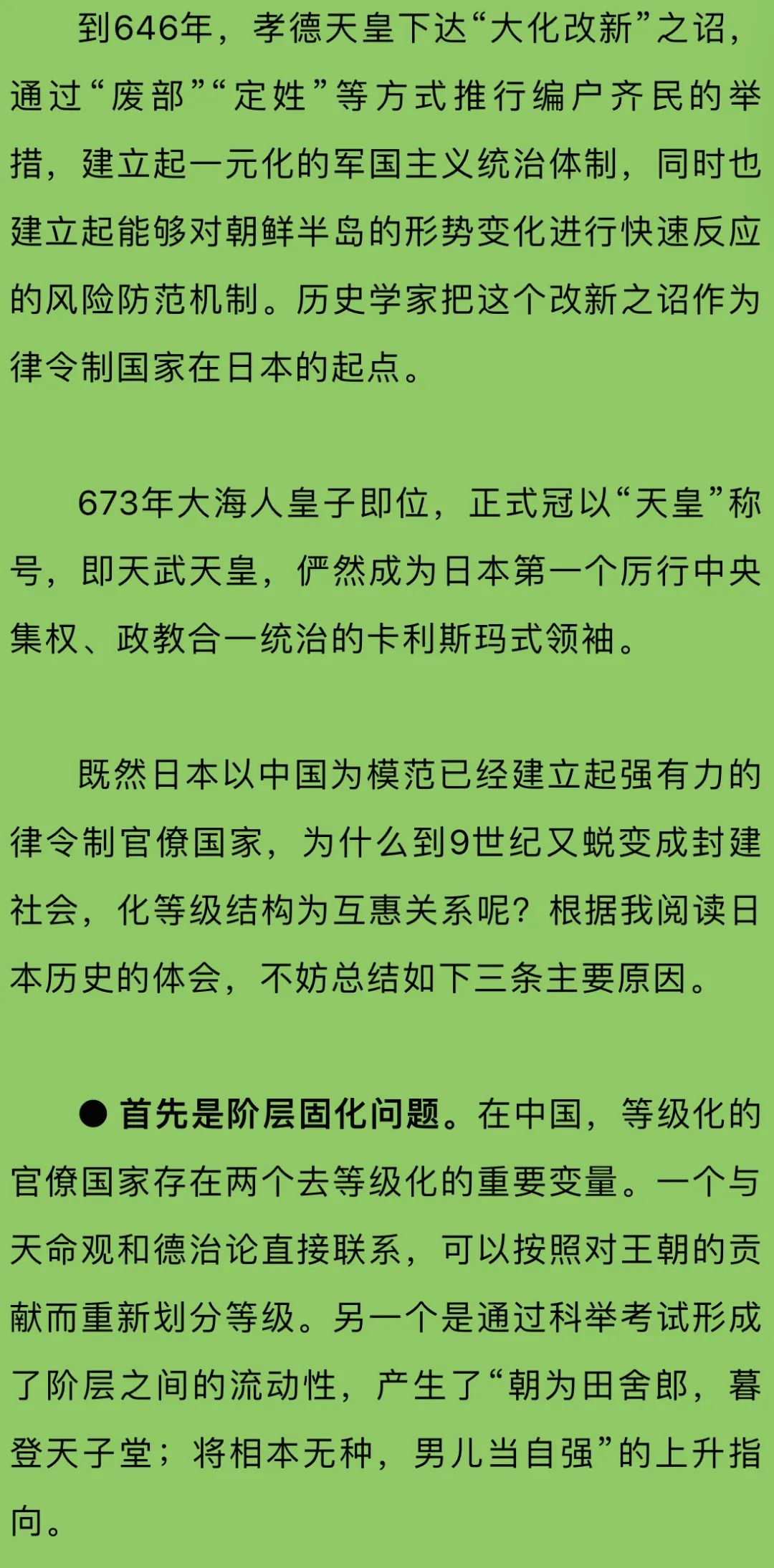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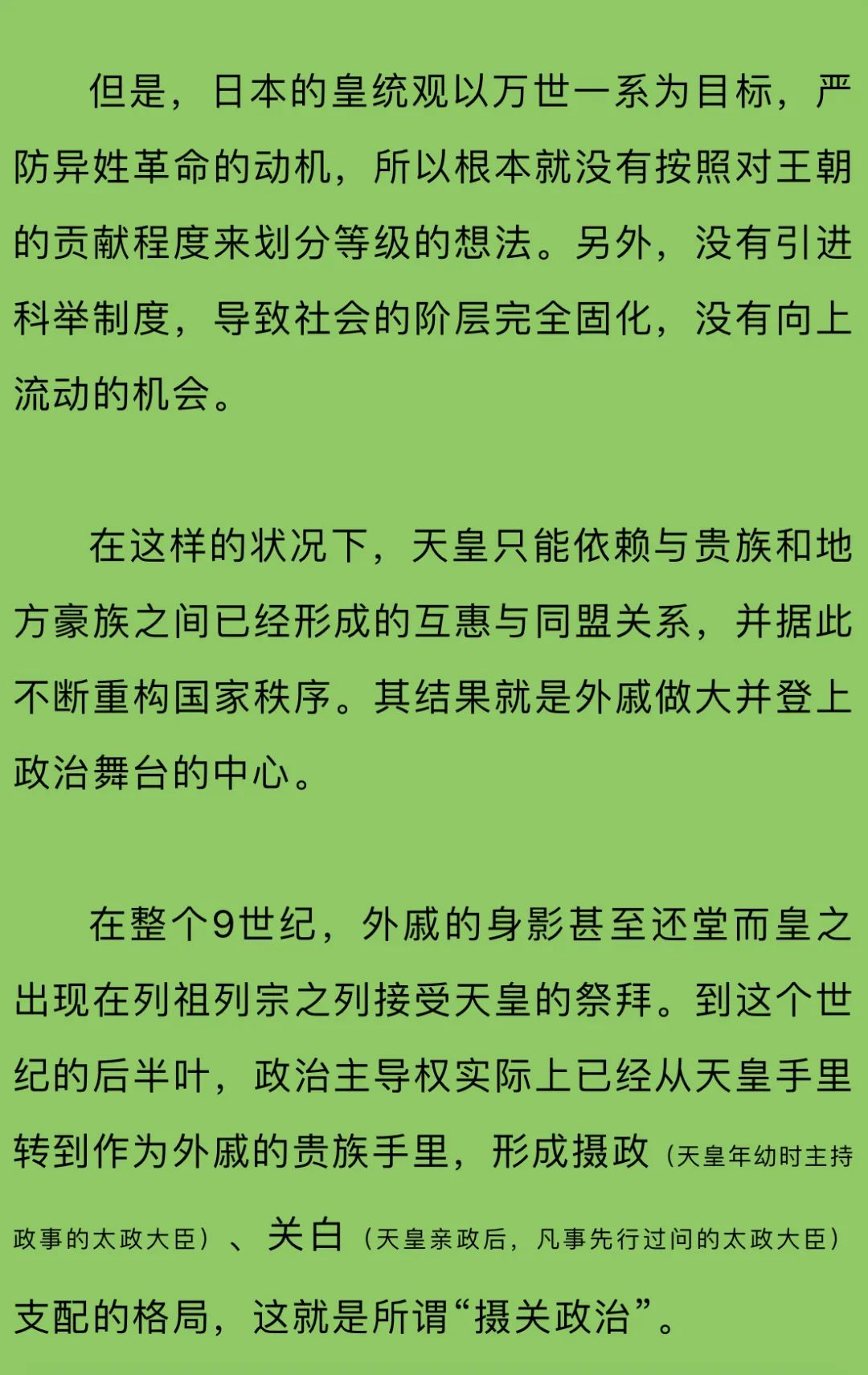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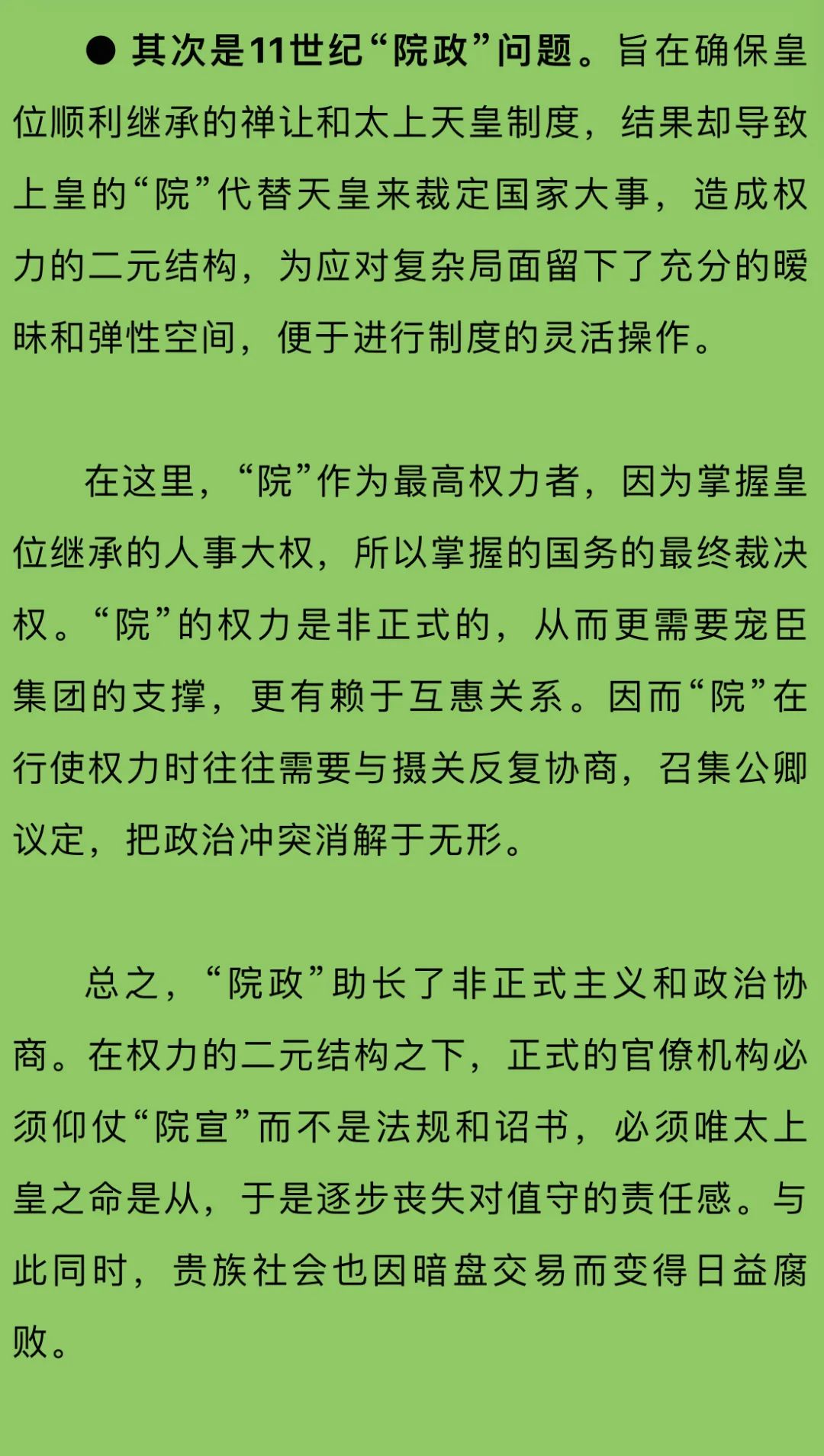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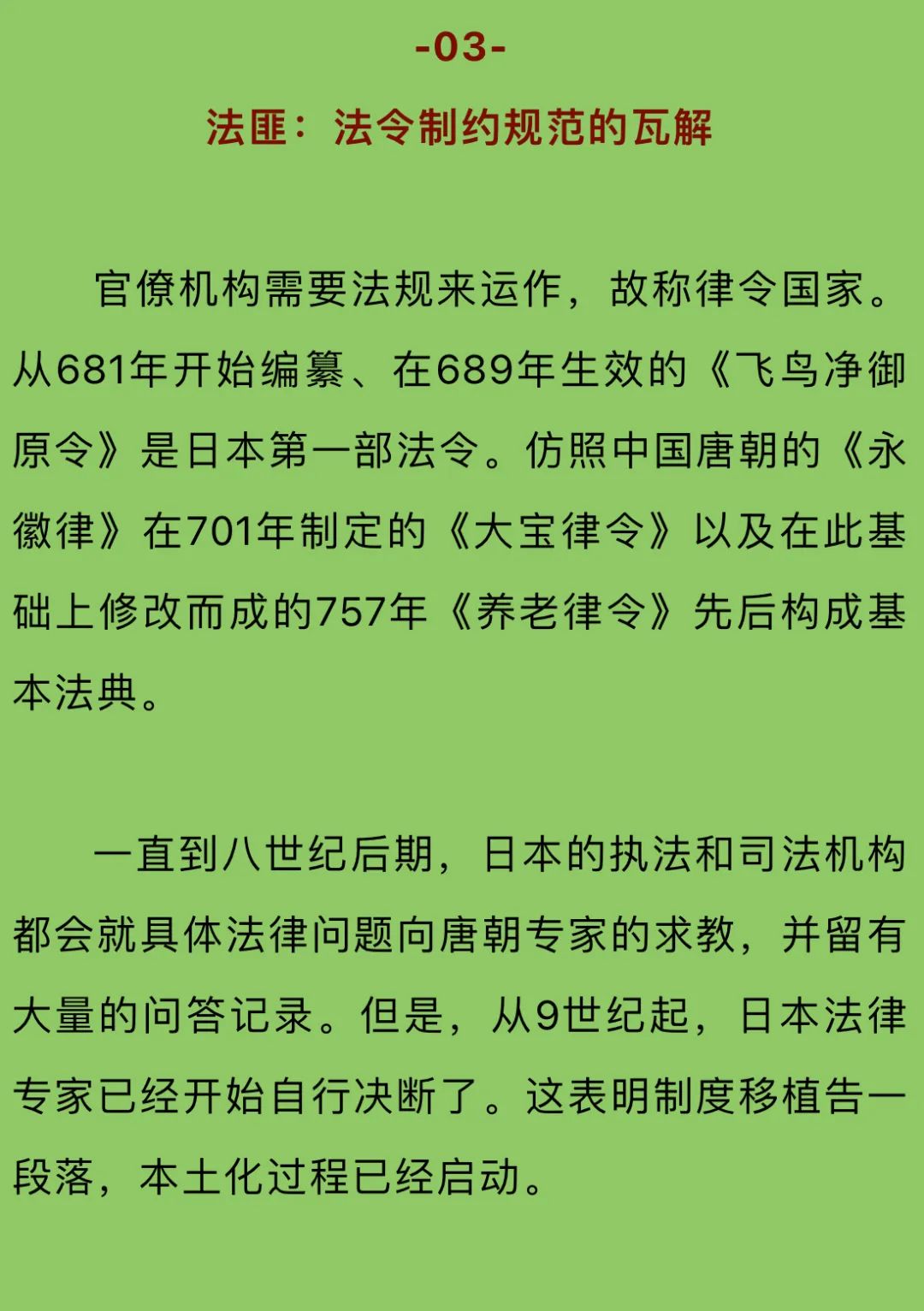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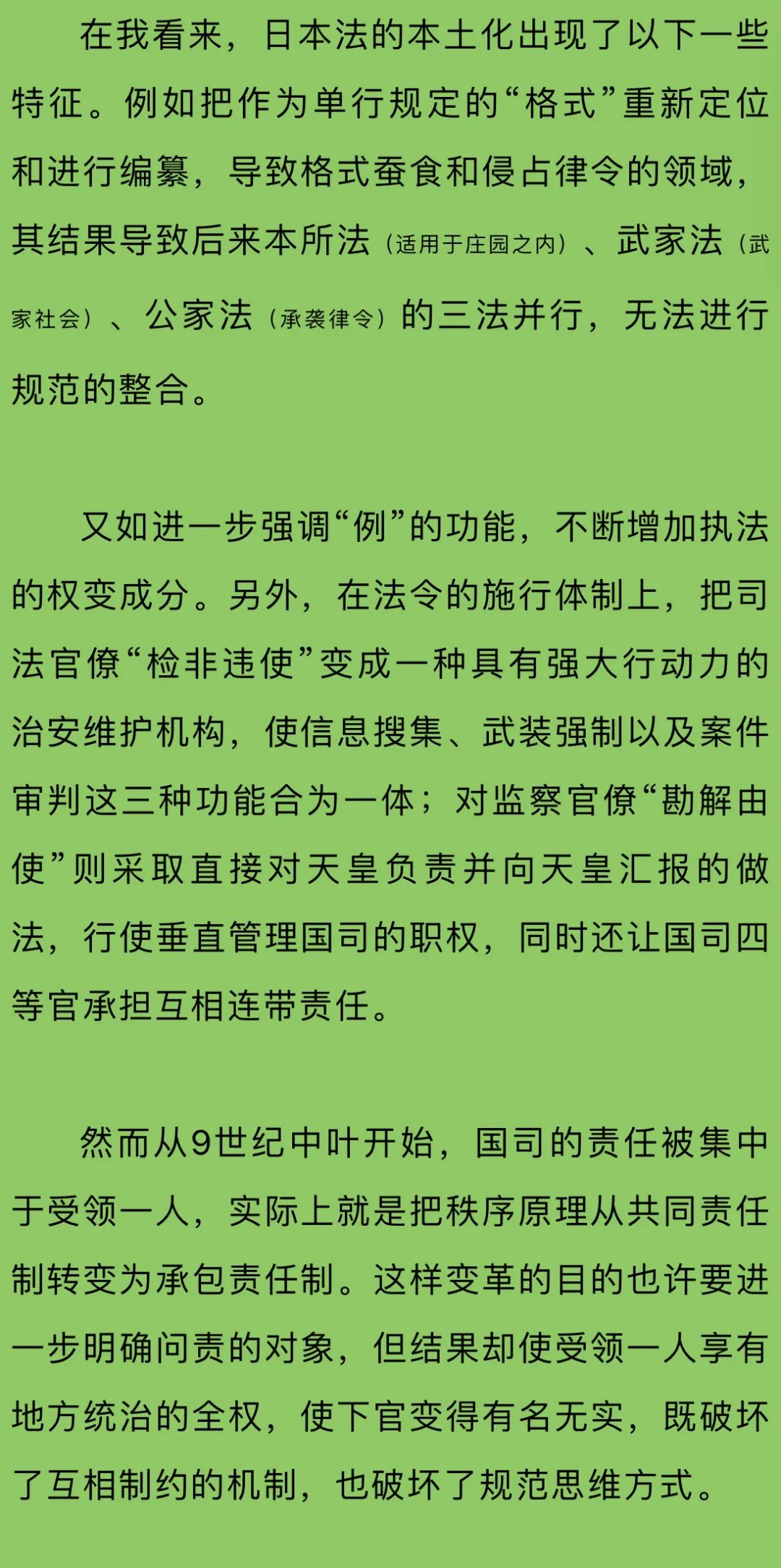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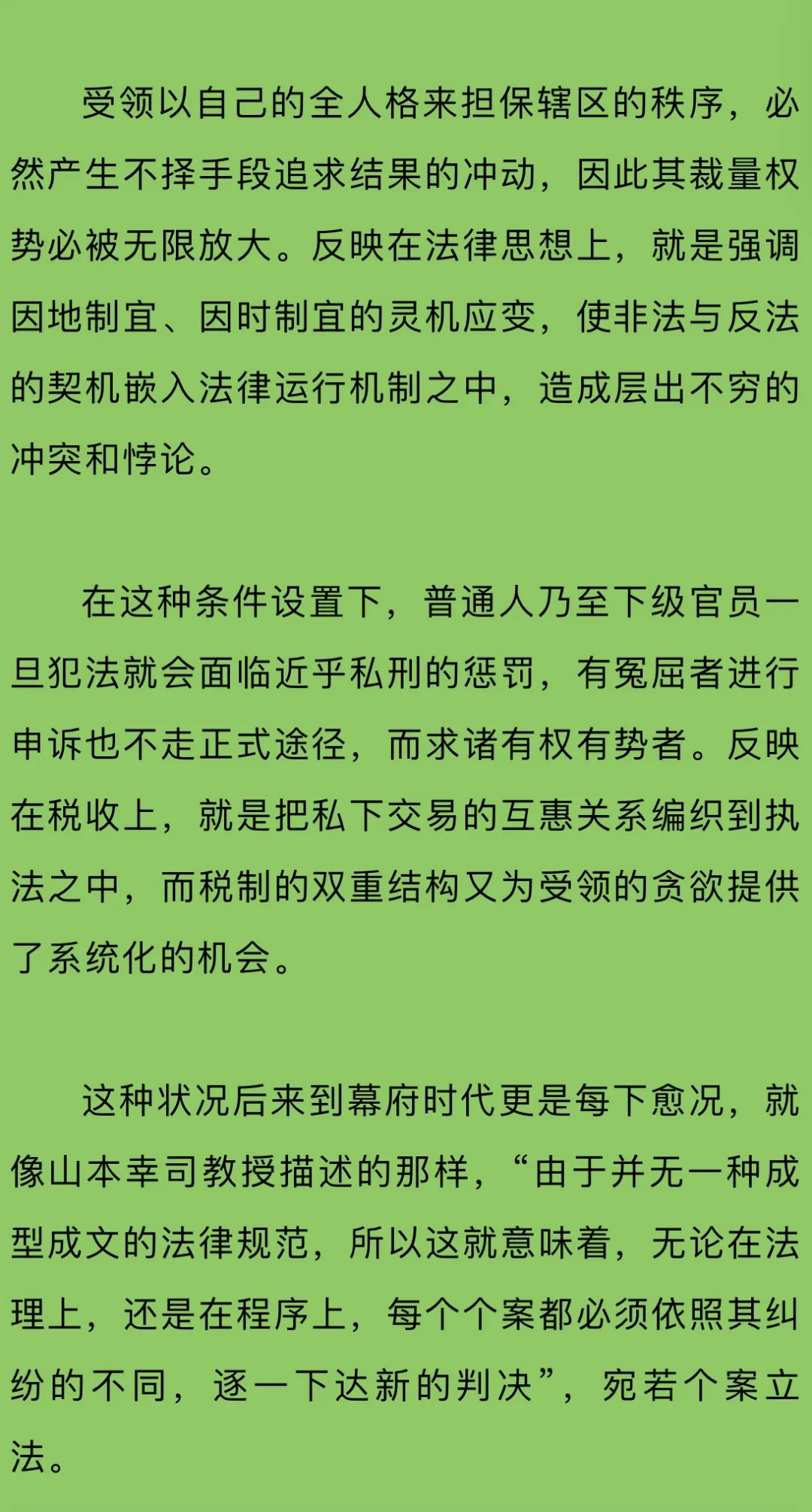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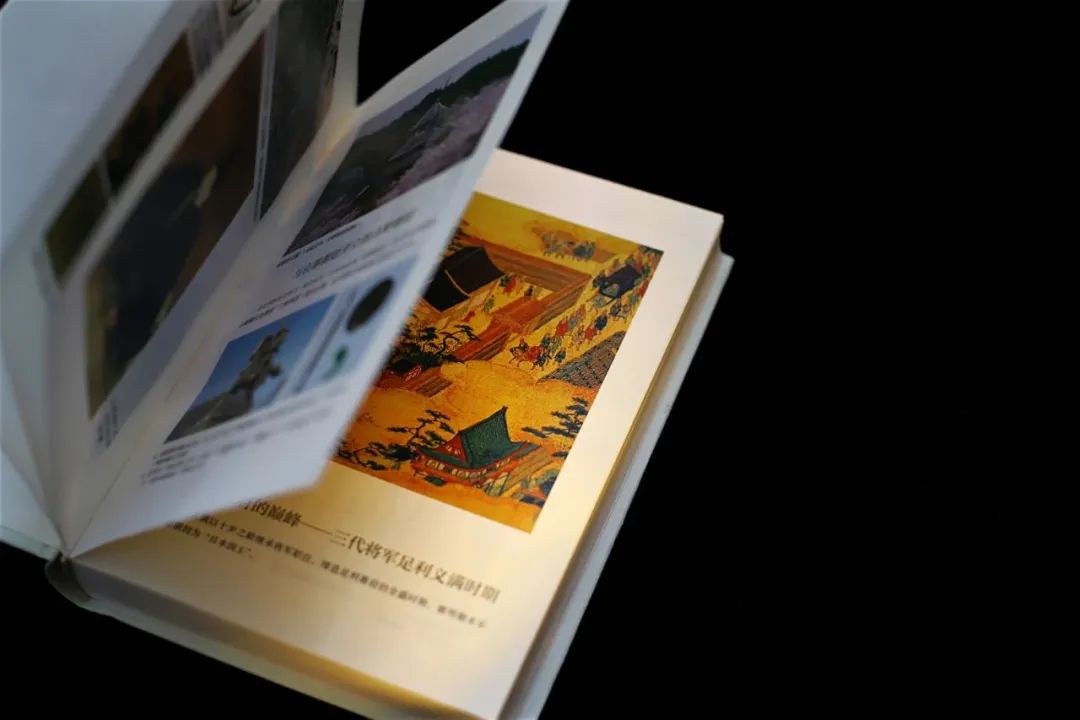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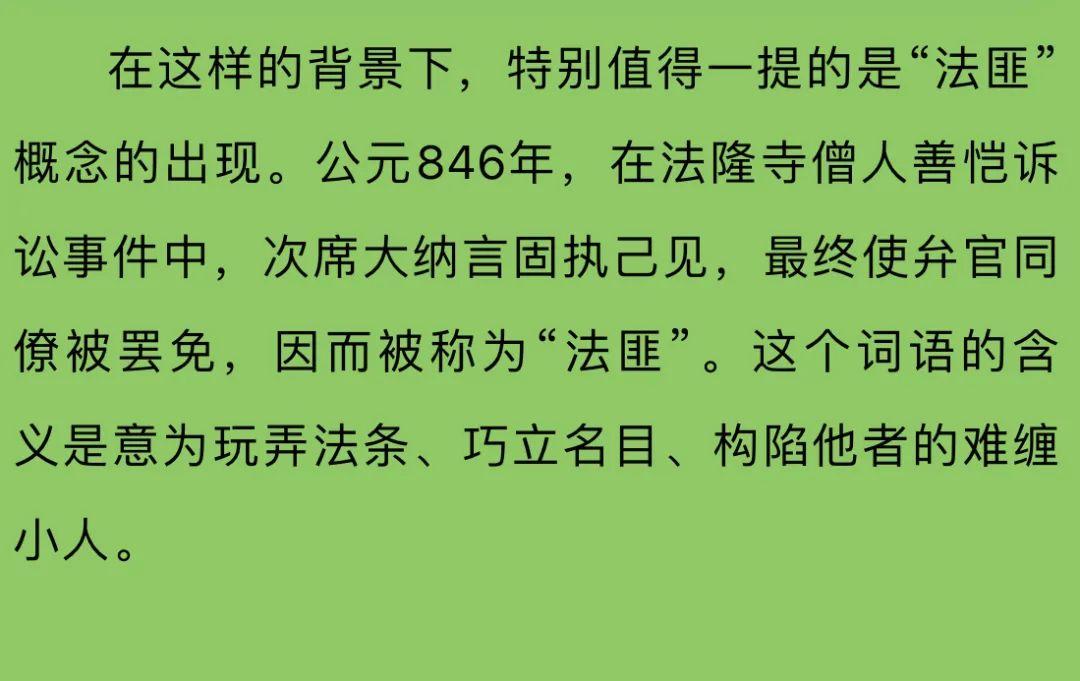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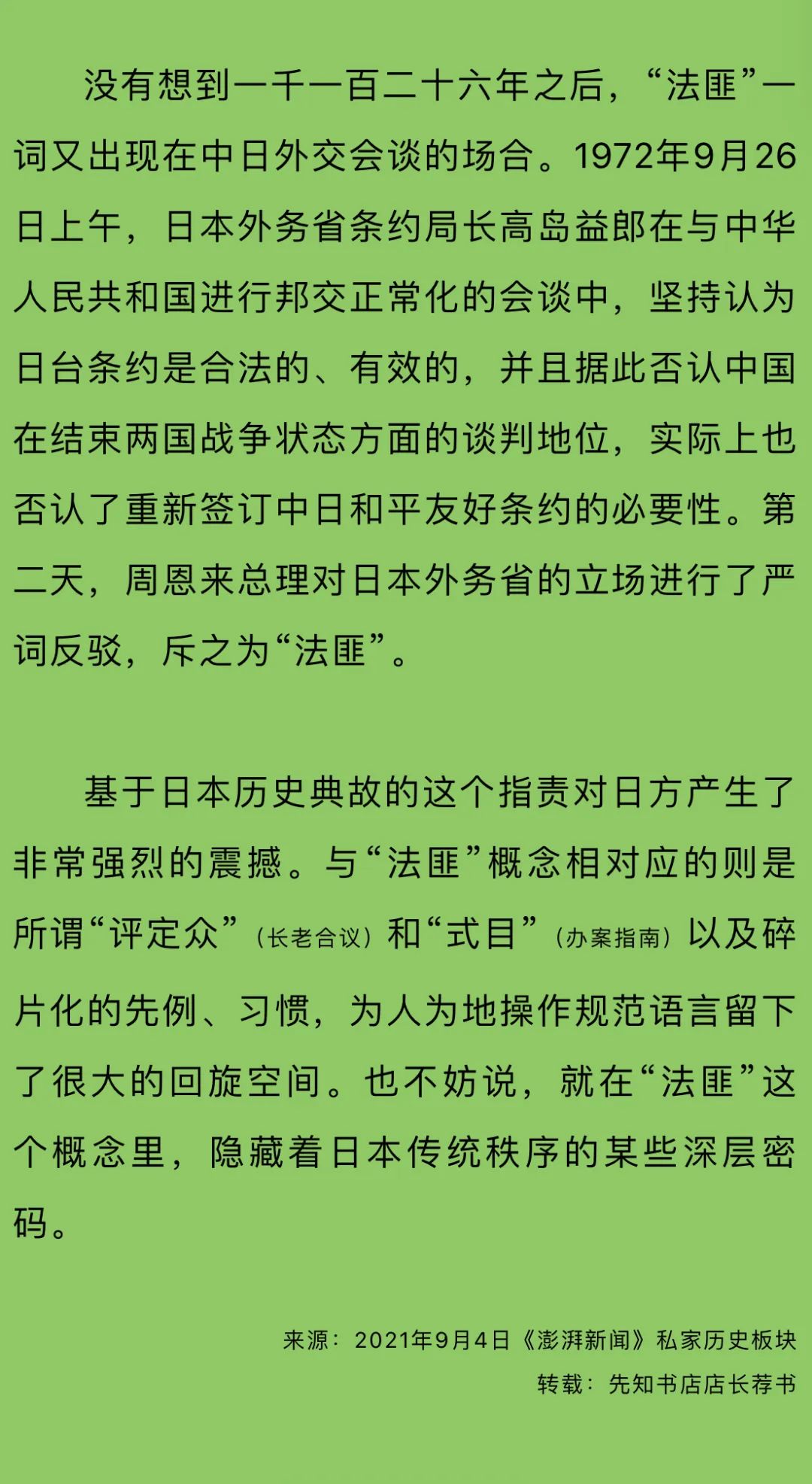
赏阅类似的妙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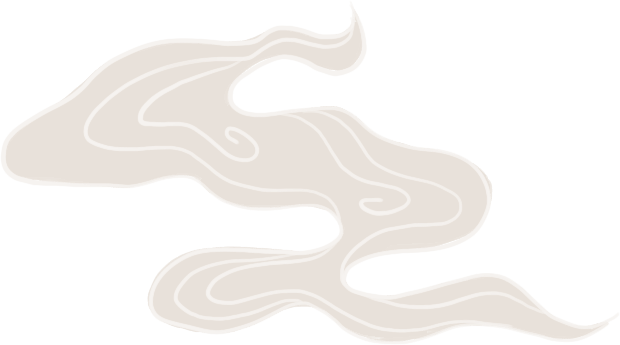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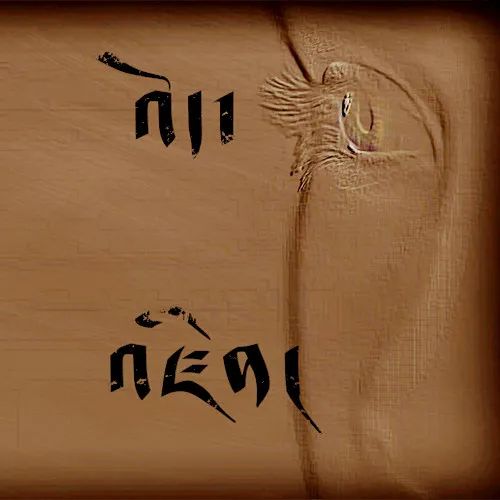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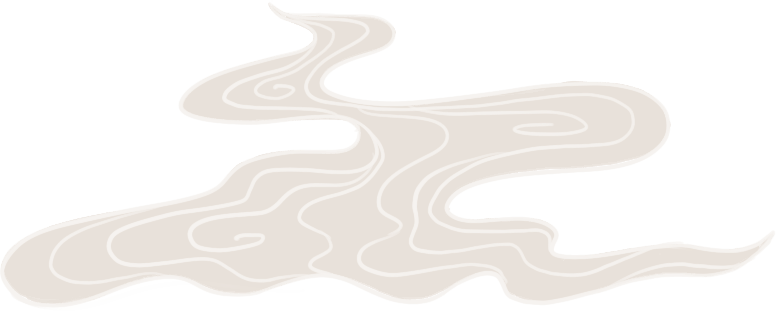
发表评论:
◎欢迎参与讨论,请在这里发表您的看法、交流您的观点。